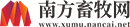(资料图)
(资料图)
凭窗而望,雪花万点,从天而降,忽急忽缓,恰似万千白衣仙子,可翩然起舞、舞姿曼妙的雪姑娘掉落下来,就不见踪影,窗前的地面变得湿漉漉的,留下的仅是一片水意。
对面楼上窗台前,刚还兴奋大叫“下雪了”的孩子扒着栏杆没找到一片雪花,悻悻然地回屋。孩子的失落感却引领着我的思绪,将我引至那曾经走过的往昔岁月。
小时候,走进“小雪”,就盼着老天爷轰轰烈烈地下场雪。有天下午,升高的气温被凛冽的北风硬拽下来,天色忽然暗下来,灰暗的天空似乎孕育着一场纷纷扬扬的雪。果不其然,晚上9点被母亲催着睡觉时,父亲拴门看到外面正下着雪就喊了一声“下雪了”,我尖着脑袋从父亲身后探过去,只见雪花飘落一层,把起伏的院墙头抹平,窗棂及门框两旁早已褪色的春联上、斜靠院墙的锄头等农具木柄上、院落里丛丛半枯的蔬菜及菊花上的雪花,经灯光的映照便幻化成美丽的灯花。“快睡觉去!明天看”,恋恋不舍地告别雪上楼睡觉,脑子里仍想象下一夜的雪,明早的雪景该多壮观!次日晨,很早起床,洒落的雪花却早已无处可寻,吝啬得不留痕迹。母亲说,不着急,进九之后无好节,不是风来就是雪。
跟随冬的脚步,雪光临的频率逐渐提高,可“三九”前的雪几乎都是水雪。记得一天上午,雪下得很大,跟着父亲出门踏雪,地上虽薄薄一层,可我小脚轻轻一踩,“噗”的一声水花四溅;目力所及,未及冬耕的农田里,错落有致的稻桩、豆菽残茎上雪色静穆,可转眼就消失得无踪无影;而田间和山边刚萌生的油菜、小麦苗的嫩叶,虽被雪染白,却从叶尖处露出绿的生机,全然不知寒冬肃杀临近;沿山脚下的泥土路回家,第一次发现雪并不是一律落在山上,而是由高及低,依次白了山体,山脚下仅有雪泥鸿爪。
与北方一团团、一簇簇、手拉手、肩并肩,浓墨重彩地从空中洒落的大雪不同,即使江南粉雪(可积能堆)下得也总是轻描淡写,温文尔雅,韵味十足,与“千里冰封、万里雪飘”的北方雪有本质区别。尤其是,江南的粉雪降临前,总要用一场场水雪做铺垫或引导,而水雪颇似江南的女子灵秀妩媚,下得细腻温润、柔软缠绵,或飘于屋顶、树枝,或黏上衣服、窗棂,雪花虽清凉,但触衣即化、抚脸即融,即便阴寒少阳的山沟,它们的生命也很短,滚不了雪球、堆不了雪人,水雪就像雪妖精一般一闪一闪地把盼雪之人诱之不放,即便“山舞银蛇,原驰蜡象”粉雪登场后,水雪依旧经常溜出来“秀”下优美的身姿。
突然,一片雪花触在脸上,令我遐思,一些往事在流年的风雪中渐行渐远,一些雪景,早已隐没于岁月的背后,只留下几纸泛黄的断章残笺。古人称小雪时节“虹藏不见”“天气上升地气下降”“闭塞而成冬”,此时该是下雪季节。此时村里的老人习惯地把双腿伸进饭桌下的火柜中,掀开搭盖的旧衣或旧被,端起老伴递来的一碗粥,热气如雾悠然腾起,米粒在碗里凝成金黄。“小雪落小雪,是个好兆头!”“嗯。”老伴附和着,院里几声狗吠、鸡鸣也像是回应。村里的老人更愿意上天按时令飘雪,正所谓“瑞雪兆丰年”。
标签: